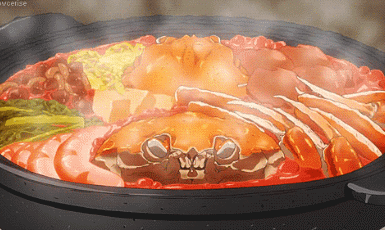文字、编辑 / 沙慧
图片 / 来源于网络
责编 / 胡晓明、黄建宁
古之前缘
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
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
——白居易《问刘十九》
最初读这首诗的时候,只新奇于“绿蚁新醅酒”,脑中自然而然地浮现出绿酒的盈盈可爱。
绿酒指的是米酒,而本以为只是用来温酒的红泥小火炉,其实是可以用来烫菜的小火锅。
天寒地冻间,邀好友共饮一壶甜酒,在火锅腾腾的热气中共话人间,已然是诗意。

火锅,起源于四川泸州,古称“古董羹”,因投料入沸汤时发出的“咕咚”声而得名。
火锅是中国独创的美食,据考证,新中国成立候出土的东汉文物“镬斗”,即为火锅。
宋代林洪《山家清供》道:“山间只用薄批,酒酱、椒料活之。以风炉安桌上,用水半铫,候汤响一杯候,各分以箸,令自夹入汤摆熟,啖之,乃随意各以汁供。”这种吃法就是“涮”。
围炉聚炊欢呼处,百味消融小釜中。
——[清]严辰
二、今之新生
从古至今,大概鲜少有人能够抵挡火锅的魅力。无论男女老少,口味如何,一顿火锅总能变幻出千种风味。
而偌大中国,从南至北的人们地域不同,火锅口味也各有千秋,更是分为了六大派别——北派、川系、粤系、云贵系、江浙系及其他。

最著名的四川重庆火锅,以麻辣鲜香闻名全国,吸引无数食客慕名前去。我也曾经无比向往去四川,只为了在烟火巷里吃一顿酣畅淋漓的火锅,才不枉在这繁华俗世间。
读霍达《穆斯林的葬礼》,其中写到韩子奇所吃的北方涮羊肉:
韩子奇坐在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北口东来顺饭庄的楼上雅座,无心欣赏窗外的雪景,眼睛只盯着紫铜火锅中沸腾的开水发愣,仿佛在研究那小小的波涛。
楞一阵,便懒懒地抬起筷子,夹起一片薄薄的羊肉,伸到沸水里一涮,两涮,三涮,在最准确的火候捞出来,放进面前的佐料碗里一蘸,然后送进嘴里,慢慢地嚼着。
他其实很饿,但仍然保持着多年的习惯,决不狼吞虎咽,也不发出“吧唧”“吧唧”的粗鄙响声。吃东西不只是为了充饥,而是一种享受,不能把好东西糟蹋了。
我也曾去饭店吃过涮羊肉,但大抵在南方不正宗,所以印象更加深刻的是潮汕的牛肉火锅。
白萝卜配牛骨清汤的锅底,新鲜的牛肉片放进锅内片刻即熟,再蘸上甜香的沙茶酱,清味隽永,是潮汕人一生追求的“大味至淡”。
在《人间有味是清欢》书中,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做《鳝鱼骨的滋味》,林清玄坐在雾气迷离的火锅店里,回忆起儿时妈妈做的鳝鱼骨汤,思及岁月如流,而生命中许多看起来微贱的东西却丰盈着我们的人生:
围炉吃火锅,是对寒流最好的准备了。在水汽蒸腾的火锅店,人人面红耳赤,有的还冒着大汗,吐出的烟气则在玻璃落地窗上结成浓浓的雾,外面的景物一时隐去,只剩下明灭的车灯疾驰照射。
我喜欢雾气迷离的火锅店的感觉,尤其是没有太多现代装潢的火锅店,依稀使人回到素朴而单纯的年代,没有那么多的商业,没有那么多的庸俗,没有那么多的烦琐与刻板。
有的,只是一片活气。
北京的朋友知道我喜欢吃火锅,特地带我去一家城西的老店,红灯笼、黄木板,每一桌上都有一座热腾腾的铜锅。锅子的烟囱高耸,烟囱的盖子大开,烧滚的锅子热汽滚滚,弥漫在整个屋子。
我喜欢火锅,不仅仅是因为其味百变,更是贪恋围炉夜话那一刻的温暖真实。即使什么话也不谈,也能在舌尖品味到生活最朴实纯真的悲欢热闹。
似乎只有在雾气迷蒙了彼此双眼,红霞飞上对方的脸庞的时候,所有的伪装都被打破,我们不设防备,连沉默都是自由。
在高考结束后和好友去吃火锅,听她幼稚地讲爱恨情仇,而我就着她的故事,看窗外行人匆匆细雨如丝,吃下热气腾腾的苦辣酸甜,然后就想着,如果时光能够永远停在这个时候,也很不错。


过年总少不了吃火锅,袅袅升起的白烟热气里,是团圆的香气,一双双筷子伸进的锅底,是亲密的相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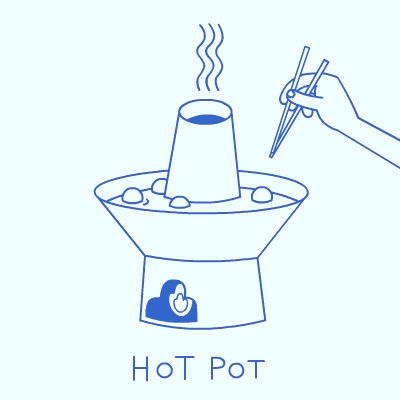
等到春暖花开、打赢病毒保卫战之时,
我们一起来吃火锅吧~